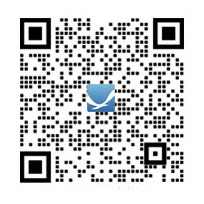??作者 | 王德培
??世界大國必然匹配全球城市。正如倫敦之于英國;紐約成長為世界城市,是美國成為世界大國的標志;東京的爆發也被視為日本崛起的象征。
??中國在2010年經濟總量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到2018年GDP超90萬億元,人口14億,從貿易量到消費量占比在全球都舉足輕重。
??以此邏輯,中國必然迎來全球城市的崛起。而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一些城市地位也確實在不斷提升。
??根據科爾尼管理咨詢公司5月30日發布的《2019全球城市指數報告》,今年中國城市在《全球城市綜合排名》榜單中取得了可圈可點的成績。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分列第9、19、71和79位,緊隨“北上廣深”的是南京,其排在第86位。此外,進入前百位的依次還有天津(88)、成都(89)、杭州(91)和蘇州(95)。
??今年的研究還顯示,中國城市排名上升勢頭不減,綜合指數排名平均得分增長速度是北美城市的3倍;在潛力城市排名中,增長速度是歐洲城市的3.4倍。
??盡管如此,中國城市離全球城市還有距離,在打造全球城市的路上仍任重道遠。全球城市的本質就是超級樞紐,那么中國到底怎樣打造超級樞紐?
??超級樞紐形成的條件
??從字面看,樞為中樞、紐為紐帶,樞紐比喻要沖之地或事物聯系的中心環節。
??放在古代,人類逐水而居,農耕文明沿江河發展,河流交匯、道路密集之處自然形成商業貿易集聚的樞紐。不管是黃河、長江孕育了中華文明,還是地中海醞釀了歐洲文明,地理條件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市的發展。
??比如,文藝復興時期興起于佛羅倫薩、羅馬等內海城市,卻也終究伴隨大航海時代的崛起而注定了威尼斯的衰落,倫敦順勢成為宏偉的大城市。
??尤其是工業革命的一聲炮響,讓滾滾車輪變成奔跑的鐵路,開始連接不同地區。麥金德就把歐亞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牧民縱橫馳騁,而今天又布滿鐵路的地區,當作世界政治的一個樞紐地區,并斷言占據東歐是控制心臟地帶的關鍵,“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進而主宰全世界”。
??之后,不管在馬漢海權論指導下美國海軍馳騁海洋,讓大量港口城市崛起,還是制空權爭奪之下的航空大發展,以致機場“大珠小珠落玉盤”,正是伴隨經濟全球化和地方城市化,世界城市網絡在鐵公機的線路交織中逐漸成形。
??尤其是中國高鐵的彎道超車,開啟了陸權復興時代,中國城市也因高鐵而更緊密,從單打獨斗到組團成群,以至原本攤大餅式發展的中心城市向網格化和多中心的大城市群轉化。
??過去40年不單城市消費、生產和交換的載體從單一到多元,從硬件到軟件,從有形(實體)到無形(虛擬),由服務地方到走向世界,中國的超大城市網絡必然產生超級樞紐般的全球城市。
??四個關鍵變量
??理論上講,超級樞紐在世界城市網絡上應是最密集、最復雜、最核心的“超級節點”。
??照常理,一般節點在平面上是兩條以上線的交叉,但超級節點并非一般節點,而是諸多節點的集成。它不能以單純平面看,而要放在立體空間中,是多條線交叉、多層面交融,由此在彼此聯系、融會貫通中形成不同“節點”,繼而從有形的交通、產業節點到無形的信息、資金節點,產生節點的疊加、融合,乃至從化學反應到生物反應。
??超級樞紐顯然在城市網絡中存在復雜層次,并產生不同發展能級,就目前看,至少有四大變量:
??一靠地緣交通,由先天位置與后天密度決定。
??最早樞紐的形成取決于其固有的地理位置,但地緣并非一成不變,因為伴隨三次工業革命,交通工具從馬驢、黃包車等到蒸汽火車、汽車輪船再到飛機、高鐵,讓人類不單掙脫固定地理束縛,更顛覆了空間區域距離,加速全球城市相互連接成網。
??尤其是交通從平面發展到立體,線路越密集,形式越多樣,流動速度越快,樞紐的集聚效應越強、輻射范圍越廣,其能級也就越高。
??二看資源配置,不止于形成要素高地,更在于系統性、生態化。
??正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城市亦如此產生集聚,逐漸走出交易中心—生產中心—貿易中心—金融中心—辦公中心的經典路線。
??但從單一到綜合,從產業橫向兼并與縱向延伸到總部經濟的成型,要素集聚也并非越高端越好,反而在于形成生態系統。因為產業偏態或整體太單一,都很難“螺螄殼里做道場”,東北城市難以大發展癥結就在此。
??三在鏈接結網,取決于城市的創新力和組織力。
??因為相較于工業時代,城市發展注重規模、受制于分工,并一心想掌控資源成為“中心”,如今伴隨信息文明改造工業經濟,城市被網格化,在物聯網武裝下充滿智慧,并能在學習中自我進化。
??以前城市競爭力看內部擁有什么,如經濟實力、資源稟賦等,現在這已非首位,更要看外部聯系與流動性。
??因為超級樞紐的戰略重要性由它的鏈接結網能力來體現,每個全球城市都將在世界流動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因而,城市只有張開所有觸角靠創新鏈接世界、組織世界,鏈接得越多,聯系越緊密、碰撞出的能量越多,就越“聰明”,進化得越快。
??四是界面關系,是否勾兌與友好。
??超級樞紐是節點集成,節點由不同線交叉,而線又由不同面交匯而成,這就涉及不同點線面之間的關系處理。僅是大虹橋的大交通樞紐若不處理好機場、軌交、公交等運力銜接與匹配就可能讓上海西大門癱瘓。
??更別提,從國際到國內,從國企、民企到外企,從中央到地方乃至區域內與周邊的關系,都需精心經營。比如政府與市場的界面拿捏就考驗全球城市的管理水平,現實是要素勾兌得越融洽、界面保持得越友好,超級樞紐上的點線面就越能合力增效,超常發揮。
??一個能呼吸、會成長的生命體
??以此看超級樞紐,既有橫向層面的疊加,又有縱向通道的交叉,還有資源集聚的磁場,更有要素流動的速度,方能成為一個實現聯動組織、功能集成的超級節點。
??實際上,超級樞紐就像一個能呼吸、會成長的生命體,道路、產業等網絡皆為血管,人流、物流、信息流等都在輸送養料。
??只不過,相較于生命體的壽命有限,城市卻能在加速代謝中持續發展。正如英國物理學家杰弗里·韋斯特所言:一座城市的經濟產出、繁榮、創意和文化都根植于其居民、基礎設施和環境的多重反饋機制的非線性特質。
??城市的產出與城市規模就呈現超線性增長,即城市人口越多,基礎設施利用率越高,比如人口翻番可能只需要增加85%的加油站。
??進一步看,城市的人口總數與其他變量間存在1.15次冪的關系。隨著城市規模擴大,城市總財富增長,人均財富的增長又吸引年輕人集聚奮斗,加速大城市的新陳代謝。由于城市代謝與其生長方程是冪律關系,越是超級樞紐,城市代謝越快。
??但通常情況下城市的維護成本與城市規模是線性關系,一旦達到臨界,能量供應不足就容易崩潰。這卻擋不住倫敦等全球城市繼續狂奔,就在于科創每次都創造新生產力重塑城市的運轉規則,使城市躍到更高軌道運轉。
??互聯網的普及用了20年,移動互聯網則只用了5年,今天AI、物聯網以更快速度侵入城市每個角落,讓城市掙脫自然增長,晉級幾何級數增長,尤其是超級樞紐將在聚變與裂變、發散與收斂、聯通與融合中進入指數級增長,并產生一種超強磁場,既能捕獲各種資源,又能高效優化配置,還能對內創新繁殖,更能對外輻射引領,牽引周邊圍繞其同步運轉,全球都能“若比鄰”般“共振”。
??城市功能之變
??由此,全球城市的競爭已非簡單爭奪資源,而是以超級樞紐打造朋友圈,就看誰的磁場更強大。
??這讓經濟地理邏輯正超越行政區劃,城市群內邊緣區有條件轉化為相鄰城市產業連綿帶的新中心,猶如細胞裂變般地生長出新的超大城市。
??如果說工業文明時代,各地通常是先發展產業再招商引資,吸引人口集聚后配套完善公共服務設施,那么到了后工業及服務體驗時代,城市競爭賽道切換到了創新和質量,發展順序從原來的“人跟著生意走”轉向“生意跟著人走”,倒逼城市先做好環境,吸引人才、機構才能衍生出創新成果和產業轉化。
??而且一般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城市發展的核心就從經濟發展轉向了人的發展。
??作為世界城市網絡金字塔的塔尖,全球城市自然將從經營城市的外在,轉向回歸其內核本質即經營人的欲望。
??放到中國看,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如今走向更高品質的城市群、都市圈發展,伴隨各大城市重新尋找個性化定位,中國的全球城市將實現梯度化、雁陣式崛起。
??只不過,當下中國上榜的全球城市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身與國內及亞太城市的強關聯性,未來需要從中心意識轉到樞紐意識(即從單向通道到多維雙向通道,從固定線性思維到流動非線性思維),強化與世界的聯系。
??以此觀之,作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龍頭,未來上海若以超級樞紐的面貌直追“紐倫港”(紐約、倫敦、中國香港),所謂卓越的全球城市也就將在水到渠成中指日可待了。
??(作者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福卡智庫首席經濟學家)
??來源:福卡智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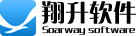


 行業資訊
行業資訊
 聯系電話: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聯系電話: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企點客服QQ:800054909
企點客服QQ:800054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