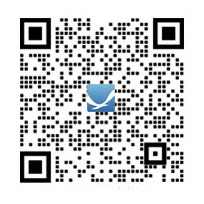盡管在住建部及八部委7月20日圈定的首批12個住房租賃試點城市中,上海不在其列,但此前半個月,上海的住房“十三五”規劃中提出新增租賃住房用地1700公頃,預計推出70萬套租賃住房。同時,明確提出“落實市、區責任,以區為主,發揮區屬國有企業功能,增加政府持有的租賃住房比例,起到托底保障和市場‘壓艙石’‘穩定器’的作用”。
再往前的7月4日,上海首次發布兩幅土地用途為“只租不售”的擬出讓地塊公告。
7月24日,這兩幅地塊被兩家上海本地國企零溢價競得。
“租購并舉,是解決住房問題的必然選擇。發達的住房租賃市場,是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重要前提。相信隨著70萬套租賃住房逐步投入市場,上海將逐步邁入租房時代。”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姚珍玲對時代周報記者總結道。
70萬套租賃住房。萬科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郁亮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這標志著一線城市正為解決居住問題做努力,而這一輪房地產行業的調控,讓他覺得像“回到了1998年”。7年前接受《中國證券報》采訪時,他亦曾表示“行業需要回到1998年貨幣化改革的初衷”。
在郁亮的回憶里,當時改革的初衷,是“啟動房地產的市場化,建立了不同類型的住房保障體系,包括保障房、經濟適用房、商品房等。那一輪改革對中國實體經濟發展帶來巨大作用,釋放老百姓(603883,股吧)的居住需求,拉動內需增長”。
中國房地產的“租房時代”,眼看著即將到來。而1998年的初衷,還回得去嗎?
福利分房那些年
“你們都羨慕我們那會兒能分房,不用自己掏錢買,但分房也真的太難了。”房價居高不下的當下,不時有人“懷念”起福利分房時代,而上海某國企退休員工吳阿姨回憶起當年感慨不已,“當時單位的房子很緊張,不是所有人都能分到的。我們家雙職工,等了6年,人均2平方米以下,1988年分到一個單身宿舍,當時兒子都3歲了。”
吳阿姨分到的宿舍在筒子樓里,不到20平方米,一層樓共用衛生間,廚房搭在走廊里,在房中間拉張簾子,隔出個小房間出來給兒子住。“螺螄殼里做道場,日子還過得下去。”吳阿姨笑著對時代周報記者比畫。
“統一管理,統一分配,以租養房”,曾是1949年以后我國實施的公有住房實物分配制度。城鎮居民的住房主要由所在單位解決,各級政府和單位統一按照國家的基本建設投資計劃進行住房建設,住房建好后,結合級別、工齡、年齡、居住人口、輩數,人數、有無住房等一系列條件分給員工居住,收取極低廉的租金。這種計劃經濟時代特有的房屋分配形式,實際上是一種福利待遇。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推進和深化,福利分房的弊端日趨嚴重。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對時代周報記者分析,福利分房跟企業掛鉤,給傳統的國有企業帶來極大負擔。其主要弊端在于,住房不能買賣,“有需求無法滿足,換工作怎么辦?”
1994年7月18日,《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出臺,象征城鎮住房制度改革之路正式啟動。1998年3月29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兩會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住房的建設將要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我們必須把現行的福利分房政策改為貨幣化、商品化的住房政策,讓人民群眾自己買房子。整個房改方案已醞釀三年多,我們準備今年下半年出臺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為商品化。”
當年7月3日,國務院進一步細化方案,以“取消福利分房,實現居民住宅貨幣化、私有化”為核心,宣布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
至此,實行近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從政策上退出歷史舞臺,“市場化”成為住房建設的主題。
改革的初衷是什么?
“1998年是我國房地產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姚玲珍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停止住房福利分配,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是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從根本上推動了住房商品化進程。對于增加住房的有效需求,啟動房地產消費市場,推動整個產業鏈的發展,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在姚珍玲看來,上海的房地產市場化改革要先于全國。“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共識,上海引發了一輪房地產發展高潮。”一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土地使用權大規模進入市場;二是,房地產企業數量迅速擴張;三是,房地產投資成倍增長,商品房開發和竣工面積直線上升。1998年之后上海房價總的來說都是處于上漲狀態,帶動了很多行業的發展,促進了就業。
“房地產貨幣化改革的初衷是為了推進整個中國發育出來一個房地產市場,使住房的提供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福利,以后不管是買房或租房,都是各人的選擇,從需求端催生了后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1998年之后上海樓市發展快速,基本上緩解了上海市的住房短缺問題。”陸銘提醒道,“跟現在上海人口增長所帶來的持續增加的住房需求相比,上海的住房供應還是不夠,房價高就是對住房短缺的反映。現在事實上房價水平已經構成對城市競爭力的影響,對吸引人才留在上海已經構成一個巨大的障礙。”
“全國接下來大力發展租賃市場,是一個肯定的事情。”陸銘指出,發展租賃市場有部分原因是為了降低城市進人的成本。“現在的做法很簡單,在批地的時候就規定未來蓋的房子只能租不能售,往這個方向走,大力鼓勵租房市場。”
兩幅“只租不售”的地塊,最終成交樓面單價分別為浦東新區5568元和嘉定區5950元,項目建成后將至少提供1897套租賃住房房源,緩解住房困難,為建立租購并舉體系提供助力。
“作為上海一批租賃用地,具有一定標桿性意義,需要國企先帶頭、先試水,待該模式運行成熟后,可能會在社會上推廣。”姚珍玲分析,這是因為國家對北京和上海的定位與其他大中型城市不同。按照規劃,上海全市常住人口規模到2020年要控制在2500萬以內,北京則要疏解非首都功能。
“在住房短缺的地方增加供應。上海和北京的住房最短缺,按道理講應該大力發展租賃市場,但這兩個城市又要控制人口,如果大力發展租賃市場,量上去了,人口就控制不住,又成了問題。”陸銘表示。
回不去1998年,但站在新起點上
與1998年剛啟動改革時的情況相似,那時,人們面對住房貨幣化改革不知應該從何做起,如今,人們面對“租售同權”不知到底該如何落地。
“以前主要是以租房為主,買房的比重不高,1998年中國開始進入住房市場化改革,商品房市場逐漸發展起來。從這個角度來講,提高租賃住房的比重,是有點這個味道。但又有本質上的不同,以前的租房市場跟單位結合,現在如果再發展租賃市場,不會跟這個結合。當年租住公房幾乎零成本,現在的租房市場基本上還是以市場價為基礎的定價—當然不排除租房市場以公租房或廉租房的形式出現,租金可能帶有政府補貼,這跟當年非常不一樣。在這個意義上來講,不能說是走向了租房市場,或者又回到1998年。”陸銘強調。
姚珍玲指出,如今希望在政策支持下發展住房租賃市場,解決一部分人的住房問題,不屬于過去的福利分房。“歷史是朝前發展的,過去是回不去的。如果說房地產市場改革,那么現在確實是一個新的起點,探索長效機制、發展租賃市場,如1998年一樣,是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大的改革。”
郁亮在前述新華社專訪中表達的觀點相似,租售并舉是建立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的重要舉措之一,如今發展租賃市場更多的是在“補課”。
- 首頁
- 關于翔升
-
產品中心
-
住建領域
- 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督管理信息系統 hot
- 智慧房票綜合管理平臺 hot
- 共有產權住房房票平臺 hot
- 智慧物業綜合管理平臺 hot
- 二手房“以舊換新”綜合服務信息化平臺 hot
- 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管理信息系統 hot
- 智慧小區綜合信息平臺 hot
- 房屋交易與產權管理信息綜合平臺 hot
- 房屋交易與產權檔案管理信息系統
- 從業主體管理信息系統
- 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統
- 測繪成果管理信息系統
- 商品房預售許可現售備案管理信息系統
- 商品房網上簽約備案管理信息系統
- 存量房網上簽約備案管理信息系統
- 存量房交易資金監督管理信息系統
- 住房租賃信息服務與備案監督管理平臺
- 房屋征收管理信息系統
- 房屋安置管理信息系統
- 統計分析與信息發布系統
- 房屋購房補貼系統
- 不動產登記領域
- 企業信息化
-
住建領域
- 成功案例
- 政策資訊
- 渠道合作
- 幫助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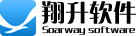

 行業資訊
行業資訊
 聯系電話: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聯系電話:059187640886 / 059188968588 企點客服QQ:800054909
企點客服QQ:800054909